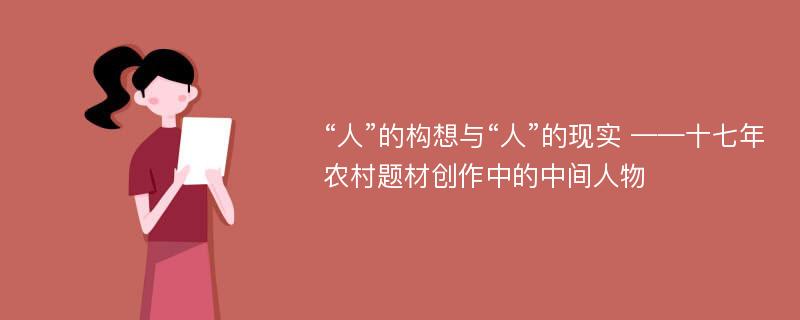
论文摘要
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是对那个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叙述,作品中的中间人物总被认为是创作者现实精神的体现。在中间人物这一问题上,人们看到了延安文艺所确立的文艺方向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一体化的努力与左翼文学内部一直存在地对文艺方向所造成的创作的僵化、现实主义的弱化的忧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过,本文则力图通过中间人物来认识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的特殊结构,以及这种特殊结构所折射出的十七年中国农村的现实图景。本论文的主体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人”的问题成为一切变革最终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的种种构想究竟怎样改变了中国人的面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性。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而言,无疑是对那个时代“人”的构想如何实现的一种“示范”,即作为被引导者的中间人物在“新人”的引导之下最终实现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上的转变。由此我们发现中间人物并非是创作者未能完整转述意识形态的愿望,而恰恰相反,中间人物几乎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必然的构成部分。第二章:中间人物的“归位”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的意义所在。在合作化运动中,中间人物的“归位”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合作化进程的认同,或者就直接表现为对合作化进程中的“新人”的认同,从而将自己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集体”。而在人民公社时代,中间人物的“归位”则表现为获得了一个固定的位置——“社员”后,一方面依旧无法清晰的知晓为集体而生的意味,一方面慑于新的权力精英的威势而佝偻着身子。中间人物的“归位”过程既折射出了十七年“人”的构想的困境,也折射出了十七年中国农民的真实处境。第三章: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中承载着“人”的构想的“新人”的所有特征并非都能够找寻到一个相对应的可供其成功“引导”的中间人物。在重构爱情的过程中,中间人物的“缺席”无疑凸显出了十七年“人”的构想的荒谬色彩。同时,孙犁《铁木前传》以对农村社会的关怀,既反衬出了那个时代承载“人”的构想的“新人”干瘪的政治符号性,也以中间人物的根本性“缺席”说明了那个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症结所在——没有“新人”,何来中间人物。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间人物是文学政治化的产物。
